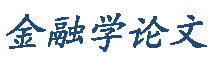【重磅论衡】韩冬临 释启鹏:40年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发展及问题
以来,中国学在研究方法的认知和应用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学研究方法体系。40年来,中国学者在学研究中始终关注方层面研究的进展,历史唯物主义、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选择、文化分析等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同时对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也表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向。但是,研究方法与应用实践之间尚有一定张力,关于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的争论一直存在,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认知与使用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学术群体的方意识仍需加强。 学的研究方法是学者们理解现象、探寻逻辑、规律的分析工具。具体来说,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指学的研究取向,即“态度、理解和实践的组合界定了学研究的某种方式”,具体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新制度主义、选择理论、行为主义、文化等分析框架。第二层面指具体的研究技术,包括定量研究、定性的实地研究、形式模型和博弈论以及实验方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和具体研究技术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取向之间也往往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初期,中国学研究并没有明确的方意识,相关的课程设置与学科建设也都是空白。而单一的研究视角很多时候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使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的现代学研究方法。以学习国外优秀为开端,40年来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经历了从译介国外研究方法到实践应用的过程。 中国学重建之初,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历史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随着的推进,我国对学的译介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达尔的《现代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秩序》、伊斯顿的《生活的系统分析》等著作的翻译出版,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学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议程,而且对国内学研究的分析范式与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的学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重视,国内对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应用相对滞后。 进入新世纪以后,夏夫利的《科学研究方法》、范埃弗拉的《学研究方法指南》、皮尔斯的《学研究方法:实践指南》、约翰逊和雷诺兹的《科学研究方法》等海外经典教材的中译本陆续出版,“万卷方法”系列丛书、“海外学研究方法丛书”、“格致方法·定量研究系列”等相继问世。以《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为代表的方研究经典的引进,则表明中国的研究者已经从关注研究方法的使用转而关注方背后的逻辑。相关著作还包括格迪斯的《范式与沙堡:比较学中的理论构建与研究设计》、戈茨的《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探讨》、吉尔林的《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等等。在学习国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中国学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 40年来,不同研究框架和研究取向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学的发展。其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的重要分析视角,行为主义浪潮在当代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义、文化主义、制度主义等研究径则为研究者分析复杂的现象提供了多元的视角。 1.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取向。初期,学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各种思想以及与阶级、、国家、政党有关的各种理论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制度,思想史和制度史等等”。这一时期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学的“五论”即阶级论、国家论、论、政党论、论。这决定了其研究大多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即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以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研究径。此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理论逐渐退出主流话语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中的应用也逐渐减少,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与结构两个维度的强调得到了深化。例如历史制度主义在中国学领域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就缘于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范式上的可比性以及命题上的可转换性。而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各种群体性事件等社会冲突及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阶级分析的研究视角再度受到重视。 2.行为主义研究取向。在中国学学科重建之时,美国学已经经历了行为主义,走到了后行为主义阶段。因此,中国学界对行为主义既有引介,也有。即使如此,行为主义在中国学界还是产生了超越其作为研究方法本身的深远影响。行为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存在规律,并且这些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因此,两者存在共性,行为主义的前提假设更容易被中国学者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行为主义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所以,围绕行为主义的讨论离不开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与引入,进而推动了具体研究方法与操作技术在中国学研究中的发展。除《文化》以及《使运转起来》等经典译著的出版为国内学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行为主义研究取向提供了极大帮助外,陈明明对行为主义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以及叶娟丽对行为主义的兴衰所做的较为深入的探讨,也都对行为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3.新制度主义研究取向。新制度主义在后被引入中国,并且在国内学界得到广泛应用,甚至有学者发现,新制度主义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少有的没有受到明显抵制的理论。制度主义的引入最初也从翻译国外经典著作开始,如《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以及“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等。其后也有国内学者专门就这一研究方法进行探讨。一般认为,新制度主义包括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近年来话语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等流派也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其中,与学最有渊源的历史制度主义在“制度回归”的学科背景下,以“径依赖”等分析工具确立其研究范式。这种与历史唯物主义有着深刻渊源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研究中国传统或者当代问题,并为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提供多元化的思考和解决方案”。制度变迁是历史制度主义者关注的重点,在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许多研究为中国的制度变迁提供了理论依据。 4.选择研究取向。广义上的选择理论包括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新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流派,而科学领域中所应用的主要是狭义的选择理论。从学科发展史来看,唐斯的《的经济理论》、布坎南和塔洛克的《同意的计算》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出版,标志着学研究中“经济学径”的确立。之后,以上述经典文献为代表的选择理论被引入国内,但在具体应用上,基于选择的研究主要存在于经济学领域,学领域的研究较少。但随着学科间交流的加深以及学者们对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视,选择视角为理解现象提供了新的窗口。 5.文化分析框架。文化既是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又是一种研究框架。后,中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有关的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专著、译著有百余种,截止到2013年,题目中包含“文化”的期刊论文已达2539篇。文化研究框架有其丰富的内涵,既包括思想史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还包括采用方法进行的文化研究。其中,有关文化的研究涉及青年、农民、公务员、少数民族、中等收入群体等。概言之,从中国学现有的研究来看,在上述几种研究取向中,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取向的研究毫无疑问占据最大比例,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其次则为基于文化和选择分析取向的研究,这反映了国内学者对国际前沿理论和方法的积极学习和应用。当然,以来,在中国学研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研究取向,例如系统分析、精英分析、国家—社会分析、治理研究、分析、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和研究径,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详述。 之初,中国学研究主要采取的是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定量研究、定性的实地研究、形式模型和博弈论以及实验方法等在国内学界逐渐得到应用和推广。 1.定量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强调定量分析方法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学的定量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态度与行为、的参与、治理等研究领域中,定量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有学者以《学研究》1985-2015年刊登的论文为例,指出其中运用统计分析的论文呈现递增态势,同时部分量化研究的论文已经不再停留于描述统计或相关性分析。在方法选择上,国内学者一般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搜集数据,用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除了最为常用的回归分析,也有研究者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公务员对参与的态度。在治理领域,定量工具的发展为评估治理绩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2.定性的实地研究。实地研究是社会科学定性分析的一项基本方法,它的兴起与中国学的发展趋势及研究转向密切相关。之初,中国学者尤其关注“”“”“体制”等宏大议题,微观研究反而十分薄弱。但随着的推进,农村地区的村民自治实践有了重大发展,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大力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社区治理、探索城市发展以及反思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也成为许多学研究者关注的议题。 早期的实地研究具有现实性、资政性和问题性等特点,主要是简单的调研与数据整理。到20世纪90年代末,学者们开始注重学习成熟的实地研究经验,借鉴规范的、科学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理论建构方法。在这种趋势下,学者们对“寻根”、村“两委”关系以及农民工子女的态度与行为模式等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的“百村观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千人百村”等项目已经建立了常态化机制,而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等机构则实现了前沿方法与实地研究的有效结合。总体而言,定性的实地研究已经在学研究的多个领域中得到应用,特别适用于基层治理的过程、机制等议题的研究。 3.形式模型与博弈论。博弈论源于应用数学领域,如今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有学者总结指出,学研究者运用博弈分析范式的理论预设、分析方法和数理模型进行学研究已经经过了试探期、成型期和常规科学发展期三个发展阶段,并且在一系列理论议题上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在中国学领域,许多学者力图基于博弈论的视角解释与行为的动因。例如,在府际关系研究中,有学者从纵横两个截面解剖间复杂的博弈关系,提出间关系的“十字型博弈”框架,并结合“府际管理”的提出了我国“府际治理”的。另有学者区分了“常规模式”与“动员模式”两种基于委托方的策略选择以及“正式谈判”、“非正式谈判”和“准退出”的基于代理方的应对策略,并以政策实施为例验证了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此外,基于博弈论的研究还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微观视角。例如,有学者通过对区域经济管理的研究指出,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最终形成的新的制度是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其中的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间的“博弈”、央地博弈、地方之间的博弈。 4.历史方法。学中的历史分析以史为重要依托。史研究吸纳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学理资源,又经历了新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员,在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发展方面拥有广阔的前景。不同于历史学中的史研究,学视野中的史研究更强调从历史上的现象及其发展演变的情况中发现运行的规律和原理。在中国学研究中,历史研究法可以沿不同方向展开。一方面,研究者可以在学理论的基础上对现象进行重述,例如有学者对中国近代两次国家构建中均选择单一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瑏瑠,还有学者对KMT两次转型中的基础能力与巩固做了研究;另一方面,研究者还可以在历史的脉络中对中国发展的独特逻辑进行新的思考,例如有学者基于对乡村史的细致分析提出“祖赋”这一概念,进而对中国道、中国奇迹予以新的审视。与此同时,随着比较历史分析的兴起,这种“结构化的聚焦式比较”具有更为规范的研究设计和更鲜明的方特性,甚至有些学者将其视作“复兴比较学的根本之道”。国内学界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已经涵盖了现代化、化、国家形成、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族群冲突等重要议题。 5.实验方法。实验方法是近年来由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既为中国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实验'进一步提更具规范性的实验性操作方法带来机遇,也为社会科学机制探索提供了新的方工具”。在实际研究中,有研究者用情景锚定法测量效能感,并探讨了该方法的优势和不足;也有研究者用列举实验法对激进行为进行了测量,检验了互联网介入对网络参与的影响。在议题设置上,关于中国的实地实验目前主要涉及行为与态度及行为两个方面。总的来说,由于成本昂贵、技术复杂、适用范围有限以及学术伦理的争议等问题,当前中国学研究中实验研究的并不多,该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应用还有很大的空间。 虽然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学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不容忽视。 首先,对研究方法自身的研究及研究方法的应用还存在不足。目前,国内大部分涉及研究方法的文献依旧以引介、评述为主,真正关于研究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有学者统计了2006至2010年“无法判断研究方文的比例”,虽然该比例从2006年的38.7%下降到2010年的33.33%,但是总体上无法判断研究方法的论文所占比例依旧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研究缺乏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意识的现状。可见,中国学界对研究方法的认知和应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科学研究方法要求审慎严谨的研究设计,然而当下很多研究都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研究中也存在研究方法的。例如,有的研究“通过数据倒推出‘故事';有的裁剪数据,或忽视事件背景,让数据服务于故事;有的通过各种数据或方法,得出各种似是而非、莫名其妙的结论”。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强调对有效研究方法的自觉应用,更要强调方法应用上的严谨性和规范性。 其次,关于定性与定量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争议一直存在。在现实层面,“中国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因此,大部分研究都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虽然在近几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来看依旧是少数。在混合方法的使用上,有学者运用混合分析方法研究了当前我国人际关系网络对社会群体动员结构的影响;有学者对91个第三波国家进行了定量定性混合分析,指出在以政党为代表的社会多元群体之间的共享是巩固和稳定新近转型国家的关键因素。当然,即便是运用混合分析方法的研究往往也只是就同一个议题分别使用两种方法,定量与定性两种逻辑之间的隔阂依旧存在。作为一种试图超越定性、定量之争的研究径,定性比较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在取得了丰硕的。基于清晰集或是模糊集的逻辑,定性比较分析在中国近几年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研究。 再次,大数据的兴起为当代学研究提供了新工具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从数据科学的角度看,大数据具有容量大、类型多、时效性高、准确性高等特点,进而产生了包括人工智能、社会计算、网络分析在内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技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计算机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发现相关的规律和逻辑,然后利用规律进行预测,从而加强了对战争与冲突等未知风险的可预测性。对国家治理而言,大数据技术有助于治理能力的提升;对而言,大数据技术使得结构化参与、半结构化参与和非结构化参与成为可能,并使之有效,参与的充分性得以体现。然而,除了基于舆情的大数据分析等应用之外,目前围绕大数据展开的学研究仍不多见。而且,大数据的分析也存在缺陷。从本质上说,大数据分析往往以相关性为主,对关系识别不足。大数据也可能导致数据,且有关数据的性与透明度不足也会影响数据信度与效度,不利于研究者对中国现象的准确把握。因此,大数据时代中国学的发展既要强化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更要从国家层面将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实现中国发展与学学科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经过40年来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飞跃式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对研究方法认知与应用的不足仍然制约着中国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已有的经验告诉我们,方之争无益于实质性问题的知识供给;研究方法只是工具,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真问题”的基础之上,并为社会结构提供实质性。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从来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方法和技术。因此,中国的学研究更需要以包容性的态度推动多元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应用。一方面,研究方法的丰富是科学进一步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科学的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在研究中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变量及变量关系,虽然社会科学研究也有数据、模型和公式等“硬”的方面,但其本质上仍属于“软科学”,这就需要学者在研究中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现“人文与科学的通融”。更为重要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带一”以及当今世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等,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更多新的议题,同时也为多元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用武之地。我们相信,在“身份意识”与“问题意识”的下,伴随研究方法的进步与广泛应用,中国学在新时代必将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注释略)梦见飞机失事 |
页面执行时间56.1856 s
金融学论文免责申明:部分资料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站长,我们会立即删除。